婆婆的言行也變得更加刺眼。她開始有意無意地念叨:「當年我懷小偉的時候,臨產前一天還在車間幹活呢!」「女人啊,不能太嬌氣,對孩子不好。」「看你這肚子尖,八成是個兒子,可得給我們周家傳宗接代。」
若是以前,我或許會內心焦慮,努力表現得更「不嬌氣」,並因為胎兒的性別而倍感壓力。
但現在,我只是默默聽著,不接話,也不往心裡去。甚至在她又一次暗示我該去託人查查性別時,直接回絕:「媽,男孩女孩都一樣,健康就好。醫院規定不能查,我們也別費那個心了。」
婆婆被噎了一下,臉色不太好看:「你這孩子,怎麼說話呢?我也是為你們好…」
我低下頭,繼續織手裡的小襪子,仿佛沒聽見。
衝突在周末爆發。
周偉的幾個朋友來家裡玩,男人們在客廳打遊戲,喧鬧無比。我孕期嗜睡,被吵得頭痛,便對周偉說:「能不能讓他們聲音小點?或者去書房玩?我實在不舒服想睡會兒。」
周偉正玩到興頭上,頭也不回:「哎呀,忍一下嘛,哥們兒難得聚一次。」
我看著他沉浸在遊戲里的側臉,心底那根一直繃著的弦,啪一下斷了。
我沒有吵沒有鬧,只是默默起身,穿好外套,拿上手機和鑰匙,平靜地說:「那我出去找個安靜的地方待會兒。」
說完,我沒看任何人的反應,徑直開門走了出去。
關門的那一刻,我聽到周偉錯愕的聲音:「哎?你幹嘛去?」以及他朋友調侃的笑聲:「偉哥,家教不嚴啊哈哈…」
我走在小區花園裡,深秋的風已經很涼了。我裹緊外套,手插在口袋裡,緊緊握著手機。
我沒有哭,也沒有特別生氣,反而有一種奇異的平靜。剛才那個舉動,像是一次小小的測試,而測試的結果,冰冷又清晰地驗證了某些東西。
他在乎他的面子,在乎他的娛樂,遠勝過在乎我和孩子的感受。
我在外面長椅上坐了一個多小時,期間周偉打來一個電話,我沒接。他發來一條微信:「你鬧什麼脾氣?快回來,讓人笑話。」
看,他擔心的還是「讓人笑話」。
我扯了扯嘴角,回了一句:「我沒事,散散心,你們玩吧。」
又過了半小時,我才慢慢走回去。

家裡已經安靜了,他的朋友們似乎走了。周偉沉著臉坐在沙發上,電視開著,卻沒看。
「你還知道回來?」他語氣很沖,「一聲不吭就跑出去,電話也不接,在我朋友面前給我甩臉子,劉婉晴你什麼意思?」
我站在玄關,沒有換鞋,平靜地看著他:「我什麼意思?我說了我不舒服,需要安靜,你有關心過一句嗎?」
「我怎麼不關心了?我不是讓你忍一下嗎?就那麼一會兒都忍不了?」他站起來,聲音提高,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!怎麼現在這麼作?」
「作?」我重複著這個字,心一點點冷下去,「周偉,我懷著你的孩子,七個月了,只是想要一個安靜的環境休息一會兒,這叫作?」
「那你也不能直接摔門就走啊!讓我在我朋友面前怎麼下台?」
看,始終還是他的面子最重要。
我忽然覺得無比疲憊,連爭吵的慾望都沒有了。
「好,是我的錯。我不該打擾你們的興致。」我垂下眼,聲音里聽不出情緒,「我累了,回房休息了。」
我繞過他,向臥室走去。
他似乎沒料到我會是這種反應,愣了一下,火氣沒發出來,堵在那裡更加憋悶,在我身後氣道:「你這是什麼態度!劉婉晴我告訴你,你別太過分!」
我沒有回頭,關上了臥室門。
那天晚上,我們開始冷戰。他睡在了書房。
躺在寬大的雙人床上,我撫摸著肚子,感受著孩子的胎動,內心一片冰涼。我們沒有再交流,連眼神接觸都儘量避免。
家庭氣氛降到了冰點。婆婆顯然知道了我們吵架的事,看我的眼神更加不滿,說話更是夾槍帶棒。公公則保持了沉默,但那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壓力。
周偉試圖緩和過一兩次,買了點水果回來,或者沒話找話地問問產檢日期,但姿態僵硬,帶著一種「我都低頭了你還要怎樣」的意味。見我反應平淡,他便也很快失去了耐心,恢復了冷臉。
我們之間那層薄薄的、維繫著表面和諧的紗,被徹底撕開了。
我開始認真思考母親的話。不再是情緒化的衝動,而是冷靜地、現實地考量。
我偷偷諮詢了相熟的律師朋友,了解了孕期和哺乳期離婚的相關法律,以及孩子撫養權的問題。律師朋友很謹慎,但明確表示,在這種情況下,母親獲得撫養權的機率極大,並且父親需要支付撫養費。
我也開始暗中整理一些東西:我的婚前財產證明、工資卡(雖然收入不高)、孕期檢查的所有單據、以及…我悄悄錄下的幾次婆婆言語刻薄的音頻,以及周偉對我冷漠相對、甚至不耐煩發火的記錄。
#圖文作者引入激勵計劃#我知道這或許不道德,但在可能到來的撫養權爭奪中,我需要證明這個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成長不利。
每一步計劃,都讓我離「周太太」這個身份遠了一步,離「劉悅媽媽」這個身份近了一步。
這個過程並不好受。三年婚姻,並非全是虛假。有過甜蜜的時光,有過相互依偎的溫暖。做出決斷,如同親手將過去的一部分血肉剜掉。
但每當夜深人靜,感受到孩子的胎動,想到她/他未來可能在這個冷漠家庭里受到的委屈,那份不舍和疼痛就會轉化為更堅定的決心。
母親又發來過幾次信息,沒有催我,只是問候身體,分享一些育兒知識,或者發些可愛的嬰兒用品圖片。字裡行間,全是無聲的支持和等待。

我知道,她在等我做決定。
轉折點發生在一個普通的周二下午。我產檢回來,有些疲憊,躺在臥室休息。周偉提前下班回了家,他似乎忘了我在家,直接在書房打電話。
書房門沒關嚴,他的聲音隱約傳出來,語氣是罕見的煩躁和不耐煩。
「……我也煩死了,天天拉著個臉,好像誰都欠她一樣…媽那些話是難聽,但忍忍不就過去了?非得較真…」
「…誰知道呢,感覺像變了個人,一點小事就炸毛…」
「…懷個孕了不起啊?哪個女人不生孩子?就她金貴…」
「…現在真是後悔,當初還不如…」
後面的聲音低了下去,我聽不清了。
但已經足夠了。
每一個字,都像一把冰錐,狠狠扎進我的心口。原來他是這麼想的。原來他後悔了。原來我所有的委屈和不適,在他眼裡都是「作」和「較真」。
血液好像瞬間凍住了,四肢冰冷麻木。心臟的位置傳來尖銳的疼痛,甚至讓我短暫地窒息了一下。
我緩緩地從床上坐起來,動作僵硬得像個木偶。
沒有眼淚,沒有憤怒。甚至沒有任何情緒。
只有一片死寂的空白。
然後在空白的最深處,一個冰冷而清晰的聲音響起:
結束了。
就是這一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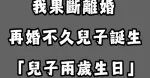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